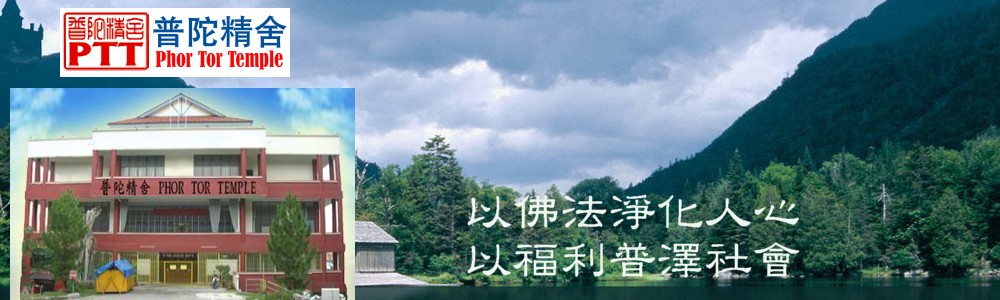|
前言
中國向來有佛教第二祖國之稱,佛教自傳入中國之後,經歷代高僧的貢獻發揚,先後成立大小乘宗派,在學術的發展上,可說是史前無例的。佛教在中國除了它本身有著特殊的成就外,它對儒道二家亦直接給予壯大的影響。道家在形式與內容上多模仿,而儒家更是盡量吸收其思想精義,以致產生宋明新儒學。可惜晚清以來,外護失勢,內弘無力;加之洪秀全所唱的太平天國,因在宗教上信奉上帝教,故對寺廟佛像,實行了徹底破壞的政策。後來孫中山先生倡導國民革命,推翻滿清,建立共和,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,佛教因而獲得了保障。隨後太虛大師、楊仁山、歐陽竟無等高僧大德,起而辦僧教育,培養住持佛教,弘揚佛法之人才,中國佛教方從邊緣復蘇過來。
以下略述影響當今佛教之相關六十年中即清末民初以後的佛教慨況:
一、 中國佛教
民國二十五年(1936年)正是中國佛教從腐化墮落階段,脫胎換骨走向新生、有為的時期。此可分作三個時期來談:
1. 舊式時代的中國佛教
民國以來,佛教領袖太虛大師,不斷倡導新佛化運動,創辦學校,推行新僧教育,發行佛刊,努力於社會宣傳佛教。可是,直到民國二十五年為止,並未收到任何實效,僧俗弟子們依然思想停留在消極,腐化的階段裡,認為“僧徒居必蘭若,行必頭陀”,“參預世事,違反佛制”。此乃主張出家僧徒必須住深山窮谷,與草木同朽,應與國家社會人群脫節的強大觀念。
2. 抗戰時期的中國佛教
民國二十六年(1937年),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由舊趨新的一個轉戾點。從這一年中,中國佛教風氣開始轉變,步上新的機運。
此時因中、日兩國入於全面戰爭狀態,太虛大師號召佛弟子們群起救亡,共赴國難,當戰爭烽火燃燒之時,全國各地佛教僧青年,應虛大師的號召,將身心性命奉獻給國家民族,為爭取自由而奮鬥,表現大乘佛教積極入世的精神。即時成立了“上海救護隊”與“佛教醫院”,療治負傷將士;以及“難民收容所”,照應三千多個難民之飯食及醫藥,一直到上海滄陷後才解散。
於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,虛大師中風舊疾復發,中國佛教頓失重心。
3. 反共時期
抗戰勝利,國土重光,經過八年的長期戰亂,中國佛教方期重建之時,不幸內戰又開始,共產黨徒談談打打,拖了三年多的歲月。在那三年當中,國事建國大業受到阻礙,佛教重建及僧徒情緒,餒糜不振,大家精神都寄望在「和談」上,希望國共和談成功。
到了民國三十八年(1949年),整個大陸滄陷,佛教僧徒逃亡,有的追隨政府到台灣,有的奔往香港或遠飄海外,因而保留中國佛教一絲慧命,佛種不致完全斷滅。逃出來的僧眾,只是衣缽隨身,但求得能活命,有飯吃有棲身之處,別無其他想。初期奔到台灣的一群義僧,被警憲當作游民看待,關進拘留所,其處境之慘,可想而知!
二、 台灣佛教
那時,大陸赴台的僧眾,尚未與當地佛教界取得聯系,一直到了民國四十一年(1952年),台灣佛教才正式有領導機構,寺僧才有了保障,但政府不太重視佛教。一個宗教,它的本身健全,固然是重大要素,可是,也還要得到政府的擁護與支持,否則就不容易發展,甚至趨於衰敗滄落。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退,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,我們佛教,如何能夠得到政府的擁護支持呢?那必須要我們僧眾發奮,不斷有所施為,而且是對國家社會人群有所貢獻。無疑地,當時抗戰延續的反共局面,一切作為,都要配合當前的反共國策,佛教在這種空氣之下,自也不能例外,對外的弘化工作,必須與政治扣緊,才能順利達成。
從民國四十二年(1953年),台灣佛教每年都有“傳戒”和啟建法會,因為這些活動是佛教內部的事,所以佛教面對社會上,一直是沉寂著。十多年內,自由中國佛教的文化工作,台灣倒是做得很好,這是唯一可取的地方。除了由大陸遷台佛教權威雜志《海潮音》之外,先後出版有《人生》、《中國佛教》、《獅子吼》、《慧矩》等佛刊,其姿態風格不一樣。除此,還辦有好幾種大專獎學金。至於佛教教育,其姿態風格不一樣。除此,還辦有好幾種大專獎學金。至於佛教教育,亦辦有好幾所佛教學校,如福嚴及其他佛學院。其最蓬勃的事業,那應是修建道場了。
三、 大馬佛教
大馬佛教的發展,可說遠在法顯法師由天竺取經歸國,途經印尼之爪哇、馬六甲,曾大弘法化。佛教從那時已有了,後因被回教傳入,代替了佛教地位。而迄今爪哇、馬六甲尚存佛教古跡。近六十年中,乃先有太虛大師率團南來訪問,後有圓瑛法師開壇傳戒,繼有轉道而過的法師等陸續興辦道場,接著是慈航法師長駐弘法,法航法師到處講學,竺摩法師創辦佛教教育。
大馬佛教有今天的成就,是從過去此些僧眾的用心,改過去一般人士對佛教誤視為迷信的污點,領導佛教在社會占有實際的地位,至使法義在群眾中生了根,信徒日漸增多,引起了廣泛的化導作用,這些都是前人所立下的基礎。當今,大馬佛教的風格,亦是過去中國佛教所未得到的成就。
在一九六六年期間,大馬佛教面臨廟多僧少,若以百廟一僧來比對,僧人亦不夠分配。原來這 多寺廟,住的多數是在家齋姑,少數為尼師。有關佛教命脈的僧寶,呈現了前面有去,後繼無人之致命打擊,往後的二至三十年當中,僧寶是一片“真空”狀態。一九八五年以後至今,僧青年逐步增多,由於中間之斷程,故北傳佛教僧團之教育,大多與台灣佛教之學習,離不開關系。
中國佛教以往的艱難歲月,是因有太虛大師作為我們的盾牌和長城。無疑地,佛教能保持今日這個局面,是仰仗了前人的余蔭,我們應該不忘前人的辛苦,應該踏著前人的足跡前進,內修外行,方能維系佛教於不墜,佛法亦能發揚光大。 |